原标题:教育时评:每个9月10日,都在提醒师道回归
师道是中华文化屹立数千年的密码之一。尽管千年前韩愈就已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但中华文化特有的“师道”,也与我们的命运一样一次次浴火,随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师道”也一定会复兴。至少,每年9月10日都是一次提醒。
“天、地、君、亲、师”。
时移世易,对于中国人而言,君权不再已百年,敬天礼地于对自然力的驾驭,唯有“亲”与“师”,还在时代的跌宕里闪转,有持守,有唏嘘。
五天之后,是9月10号,从1985年起始的第三十个教师节。这三十年,教师这个古老的职业从谷底一点点向上回升。经过30年“重教”的,教师总体上已算体面,尤其名校教师待遇更是令人艳羡。然而另一方面,教师这个职业的美誉度,却包含着复杂的况味。
设立教师节的初衷:
历史的线在某些脚本上很有规律:对教师的不尊重,以30多年前为极,对教师的再尊重,以30年前一个节日的设立而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教育工会恢复了活动,我担任。当时受‘’的影响,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极其低下。从1979年起,在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我们致力于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试点工作,举办‘教师暑期活动’和‘庆教龄’等系列重教活动,旨在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要让教师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的尊敬,还应该在新中国建立教师节。”曾担任全国教育工会的方明老人生前回忆道。
方明17岁师从陶行知,是教育救国的遵从者。他曾在岁月中领导上海地下党教师工作11年,曾担任全国教育工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促进会第十届会顾问。而他,也是第一届教师节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1981年初,当方明带着上述感慨把这一想法和当时民进中央的主要领导沟通时,得到了一致赞同。他们当即决定通过参政议政的方式促进教师节的设立,推动社会重教的风尚。于是,在1981年3月的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方明等民进组17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的提案。
除了方明,在提案人中,有民进中央第三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副叶圣陶;民进中央第四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副、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曾任民进中央副的徐伯昕、吴贻芳、葛志成、叶至善;还有曾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的养、柯灵。同时,方明是提案的主要发起人及撰稿人。
1981年12月,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方明和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一起又提出设立教师节的事。
“当时,领导同志问我,解放前有无教师节?我说解放前的教师节是6月6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6日上海教师们在大上海戏院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教师节。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领导同志听完我的介绍说,你们两个单位联合起来写个报告,请示中央。”
1982年4月23日,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联合,由张承先和方明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到了中央处。
“为教师节定在什么日子最合适,我征求过谢冰心、叶圣陶等民进老前辈的意见。冰心先生定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定在每年学生入学的日子,让学生在新学年的开始就记住教师的辛勤和光荣。”
1983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方明和民进18位政协委员再次提出“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重教的社会风尚,恢复教师节案”。
最终,1985年1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当时我们的钟敬文先生不上台,总理和其他的领导甚至推迟了一会开会也要把他请上台来。钟先生是1925年的教授,我们当时觉得这个行为也是在领导层对于一个老教授、老教育家的尊重。”语言大学的学生,他至今仍记得在北师大东操场庆祝1985年第一届教师节的情形。
“我们在回宿舍的上一直在议论总理的讲话,当时听起来抑扬顿挫,像是发自内心的对于我们这些教师,或者说未来教师的一种真诚的祝福,”他说,“这个东西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记。”
原标题:教育时评:每个9月10日,都在提醒师道回归
教师地位的变与不变
尽管30年来,对于很多老教师来说,“这个东西”一直没有被忘记,但时间总还是能淘洗掉很多东西。
“教师节在当时还是起到一点作用的。”胡朗老师回忆起最早的教师节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时说,“因为当时人们对教师这个职位没有那么重视,工资也比较低。那之后,教师工资也相应提高了,因为教师节不光是一个节日了,它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了,它底下干的实事更多,比如说对教育的投资啊,对教师的待遇啊,都有很大的区别。到现在形式上的东西好像没有了,但是实质上的东西还有很多。”
胡朗老师现在是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物理特级教师,回顾自己的经历,他说,这些年的教学生涯,是从上世纪89、90年左右开始找到职业成就感,从那以后“越干越来劲”。那两年,他还在山西的县里教书。从那时候起,他先后评上了市级劳模、山西省劳模,也是第一次被评选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现在作为特级教师的胡朗已经把荣誉和待遇看得很淡了,但无可否认,上世纪80年代末的他,对于荣誉仍然有着非同一般的期待。
某中学从事教学多年的陶彬老师(化名)现在看待教师荣誉和评价标准时,则显得现实很多。“过去的特级教师很少,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制度,每三年都要评,现在这样的教师太多了,而物以稀为贵。”而对于这种教师评价标准,陶老师归结于“社会变了”,“过去评价一个老师是看他敬业,现在特别注重师德”。
而同样是在这个国家,不论是教师节,还是荣誉、待遇,或者每三年评选一次的大城市里的“特级教师”,都与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广西大山里的韦凤花老师都没有什么关系。
每天天蒙蒙亮,韦凤花就早早起床洗漱。在把这座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停当时,她的32名一至二年级的小学生也陆陆续续来到学校,韦凤花的一天就这样开始。
“教师节?教师节和我没有太大关系吧,它是表彰那些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老师。哎呀,怎么说,我工作也是一般。”2014年的“教师节”已经是韦凤花度过的第23个“教师节”了,但问起韦凤花的感觉,她始终觉得节日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
1991年,韦凤花高中毕业不久成了一名代课老师,“那时候叫‘民办教师’,当时说,两年后参加考试就可以转成‘公办教师’。”但事与愿违,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获得函授文凭的韦凤花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花了23年。
2013年8月底,韦凤花来到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勇村弄顶教学点来当老师时,她心里是踏实的。因为不久前她终于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正式教师,结束了22年的“代课老师”生涯。那时候的幸福感,要比问起她教师节有什么感受实在得多。
带着这份“久违的幸福”,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成为正式教师的最后条件:到100公里以外的山村小学教学点工作3年—她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确艰苦,但总是要有人来。”
从胡朗到韦凤花,这之间不仅仅是教师节从大城市“重教”到山区民办教师现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城的喧嚣到广西偏僻大山之间的时空距离,而是陶彬老师那句很简单的总结—“社会变了”。
社会变了,社会也没变。北师大附中特级教师胡朗说,70年代初他在农村教书的时候,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农民在地里耕田,看到牛不走了,就说,这是想要歇着当老师去。“他以为老师是歇着的,就是不用劳动的,”胡朗说。
而这个笑话所嘲弄的某些东西和对老师这个职业的轻视,至今仍有市场。人们会心一笑时,挂在嘴角和心头的某些东西,变了么?
未必。
原标题:教育时评:每个9月10日,都在提醒师道回归
“师道”回归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很多事情的改变与不变大抵如此,回过头来,它还是它,变得是自己。而这份繁复与简单的间隔,时如天堑时如细线。
对于教师群体而言,改变的,其实是大众。对教师印像的所有变化,映射出的也是社会大众心理的变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最普遍意义上“好老师”的判断标准,而在学生家长看来,时下究竟什么是“好老师”?
的学生家长钱女士(化名)这样回答:“对‘好老师’的评判标准我觉得可能更多来自于另一个含义的‘学高’,就是升学率的高低,而‘身正’在当今教师队伍里的缺失已经让兼具‘师德’的好老师显得弥足珍贵。”
“从孩子2004年上幼儿园开始,我接触的大多数老师曾一度让我质疑教师的整体素质,而这些老师基本上都是区级甚至国家级重点学校的教师。特别是教师节期间,大多数人都是公然收受家长学生所赠的贵重礼品……一些老师还会很认真地分析每一位家长的优势,然后集成利用(最不济的家长也能被利用为班级复印卷子等)。”
钱女士说,老师的这些行为让家长在家庭教育中花费了大量精力为孩子建立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家长的)苦口婆心抵不过老师一个负面的行为示范”。而事实上,这种问题令人吃惊之处在于,老师的“负面行为示范”丝毫无法引起人们的吃惊:家长们时有抱怨,然后继续波澜不惊着,苦口婆心着……
那么老师又是如何看待时下的家长呢?
“家长们认为中小学教师直接影响孩子能不能考上重点中学、大学,因此对他们更为求全责备。而社会好像有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一个孩子能不能成才,成多大的才,(在家长付出了物质报偿之后)全是学校和教师应负的责任了。”河南商丘市梁园区某高中的小赵老师说。
在年轻的小赵老师看来,她所进入的已经不是自己印象里相对单纯的校园生活了,“孩子都或多或少过早地进入了化的世界”:你表现得成熟点,学生觉得你;你稍微童真点,他们又觉得你幼稚、不切实际。
“我们这里的师生关系更像是社会的缩影,”小赵老师说。
而什么是社会呢?对于老师而言,更多的,是家长。
知名教育学者储朝晖的判断正是基于这种相互纠缠的状态—“以功利给教师送礼,本质上是通过礼品教师,让教师成为自己的工具”。于是,你所利用的人,也就成了功利化联系的一部分。
“这是对教师最大的不尊重和不理解,”储朝晖说,“功利化的社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回归‘师道’。”
但是,怎么定义“师道”?
或许答案是,我们毫无必要去定义什么干巴巴的“师道”,我们只需要知道,什么不在它之内,哪些值得我们尊敬,以及我们能做什么。
也许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的说法反映了某种现实:“从1994年《教》颁布至今,(我国的)教师形象是日益变得模糊的。相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教师群体的教育理想、人文情怀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职业倦怠感和整体的功利价值取向。”
“要让教师群体有一个清晰的社会形象,应该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和功利化,按教师职业属性建设教师队伍,保障教师的职业待遇和教育自主权,让学校回归教育属性”,这是熊丙奇给出的解决之道。
然而这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教师首先是一个人。而当他人成为你自己的投射时,一切的解决办法,是从扪心自问开始的,包括我们,包括老师。
偏僻山村普通教师韦凤花说,“这里的确艰苦,但总是要有人来。”
某中学教师陶彬说,“我小时候想当老师就是觉得能管人,后来自己当老师之后发现自己绝对是特别尊重学生的,因为这样学生才会尊重你。”
师道者何?为人而已。(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小舒 刘小草 强晓玲)(新华每日电讯)
延伸内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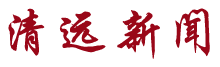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